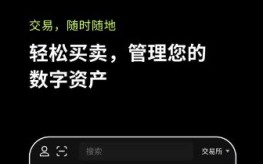作者:Be Water
编译:深潮TechFlow
《投机攻击》第三部分
咆哮的 20 年代
在金融市场中,狂热情绪往往具有强大的既得利益驱动,即使这种狂热接近疯狂状态——正如1929年的情况那样。对于任何评论或撰写当前金融市场趋势的人来说,这无疑是一种警示。然而,在这些问题上,确实存在一些不可忽视的基本规则,忽略这些规则的代价绝非微不足道。而最为受害的往往是那些对所有当前警告嗤之以鼻的人。
——JK 加尔布雷斯(JK Galbraith),《1929 年平行线》,《大西洋月刊》,1987 年 1 月,1987 年大崩盘前
虽然比特币财库公司目前只是庞大的金融矩阵中的一个小瑕疵——而且,在 Fartcoin 市值高达15亿美元的情况下,仔细研究它们似乎有些荒谬——但它们与 1920 年代投资信托的相似之处,却揭示了超越其当前规模的反复出现的投机病态。事实上,它们为普遍存在的反射性泡沫提供了一个通用的蓝图。因此,信托和财库公司之间共享的机制提供了一个完美的视角,让我们能够更广泛地理解金融历史以及当前金融矩阵中正在发生的动态。
在《投机攻击》第一部分中,我们探讨了迈克尔·塞勒的 MicroStrategy 如何通过颠覆风险炼金术,将华尔街自身的金融工程武器化,以对抗传统金融体系;现在数百家公司竞相复制他的蓝图。
《投机攻击》第二部分探讨了当今比特币财库公司与 1920 年代“投资信托”之间的相似之处。这些信托起初是英国备受尊敬的投资工具的变形版本,但被美国金融家通过杠杆放大后逐渐变得腐败。到1929年年中,信托狂热达到了顶峰。高盛(Goldman Sachs Trading Corporation)成为当时的“MicroStrategy”,而新的信托每天以一个的速度推出,投资者热情高涨,愿意支付其基础“稀缺”资产价值的两倍甚至三倍。
然而,像比特币财库公司这样一个充满未来感的概念,怎么可能与 1920 年代的金融信托有任何关联呢?在那个年代,计算机技术尚未普及,更不用说区块链了,证券交易委员会(SEC)甚至都还没有成立,更不用说开始遏制华尔街那些花里胡哨的滥权行为了。乍一看,1929年的信托和如今的财库公司之间在结构上的差异似乎既显而易见又不可避免。
我们认为,这些差异在本质上并不重要。金融史上的每个时代都在其独特的背景下展现出自己独特的特征。过分关注表面区别是人类长期以来对基于历史教训而发出的有关新兴金融风险和过度行为的合理警告的合理化解释。市场参与者对待每个事件都仿佛是人类第一次遭遇金融炼金术,无视《愚昧的大镜子》(Great Mirror Of Folly)(1720 年)中记载的“对后世的警告” 。然而,这种方法无异于准备打最后一场战争,而不是努力掌握持久的战争原则并将其应用于当前的战斗。
近几十年来,这种模式在多个领域中表现得尤为明显,从“私人信贷”到数万亿美元的负收益债券,再到澳大利亚、加拿大、瑞典和英国历史上曾肆虐(如今似乎正在消退)的房地产泡沫。以这些房地产泡沫为例,市场参与者例举出,缺乏复杂的美式衍生品(如CDO、NINJA贷款)、猖獗的欺诈行为、无追索权贷款以及在2008年金融危机期间的银行倒闭,以此来打消人们的担忧。就像对香槟要求必须来自法国特定山坡的纯粹主义者一样,如今许多人认为只有具备《大空头》(The Big Short)所流行的次贷危机典型特征——包括在拉斯维加斯吃寿司的CDO立方经理——房地产泡沫才算真正存在。
电影《大空头》(The Big Short)片段节选
其结果是一种历史的字面主义:结构差异被视为安全的证据,而事实上,这些差异往往被夸大、误导,或根本不相关。例如,在实践中,上述每个国家都只是发展了各自独特的机制,发挥着类似炼金术的功能。
比特币财库公司的支持者也提出了类似的论点,他们认为,将比特币财库公司与 1920 年代的投资信托进行比较存在根本性缺陷:这些信托建立在不透明的金字塔结构、隐藏的杠杆和不受监管的市场收费之上,而比特币财库公司是透明的单一实体公司,没有管理费层,且受现代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信息披露规则的约束,并持有目前最理想的市场价值资产。简而言之,他们认为,任何表面上的相似之处都掩盖了结构、代理关系和信息流方面的深刻差异。
虽然我们认同其中一些观点——即便不是全部——但我们仍然得出了不同的结论。引人注目的事实并非比特币财库公司与 1920 年代的信托之间存在如此大的差异,而是相同的基本面动态反复出现——这使得它们之间更深层次的相似之处令人无法忽视。两者都具有巨大的资产净值溢价、“增值魔力”以及反射性反馈循环,在这种循环中,购买会推高基础资产价格,从而提升其自身价值和借贷能力。这两个时代的投资者都拥抱“睿智的”的长期杠杆,以及通过金融炼金术轻松赚钱的诱人承诺,以利用“稳赚不赔”的赌注获利。
这些模式不仅仅代表着历史的相似之处,它们揭示了人性和金融反身性的永恒不变,而这些正是信贷泡沫的根源,超越了时代和资产的限制。因此,这些早期信托的命运提供了一个客观的视角,让我们不仅能够审视新兴的比特币财库公司现象,还能洞察定义数百年来泡沫形成的金融炼金术的反复出现。
Twitter/X: @bewaterltd 。有什么建议?欢迎反馈。
并非投资建议。仅供教育/信息参考之用。请参阅免责声明。
“投资信托如蝗虫般繁殖”
比特币财库公司的爆炸式增长与 1920 年代的投资信托如出一辙,这两场淘金热都源于一场完美的贪婪风暴:投资者对稀缺资产的强烈需求催生了资产净值溢价,而发起人则争相将其变现。如果高盛在 1920 年代都能从其信托中攫取巨额利润,为什么其他公司做不到呢?如果 MicroStrategy 能够将其资产净值溢价变现,为什么其他公司不应该效仿呢?
加尔布雷斯(JK Galbraith)记录了 1920 年代信托的爆炸式增长:
1928 年 ,估计有 186 家投资信托成立。到 1929 年初,这些投资信托的成立速度大约是每个工作日一家,全年共有 265 家投资信托成立。
筹集的资金规模同样引人注目,占 1920 年代所有发行基金的 70%。仅 1929 年 8 月和 9 月,新信托发行就达 10亿美元——按今天的购买力平价计算,相当于 200 亿美元,或占当今经济总量的1300亿美元:
1927 年,这些信托向公众出售了价值约 4 亿美元的证券。1929年,它们出售的证券价值估计达 30 亿美元。这至少占当年所有新发行资本的三分之一。
到 1929 年秋,投资信托的总资产估计已超过 80亿美元,自 1927 年初以来增长了约11倍。
资料来源:DeLong/Shleifer
弗雷德里克·刘易斯·艾伦(Frederick Lewis Allen)的记述证实了加尔布雷斯(JK Galbraith)的说法;在《昔日岁月:1920 年代的非正式历史》一书中,艾伦(Frederick Lewis Allen)生动地描述了“投资信托如何像蝗虫一样成倍增加”:
据说现在有近五百家这样的信托公司,总实缴资本约三十亿美元,持有股票约二十亿美元——其中许多股票是以目前的高价购入的。这些信托公司中既有管理诚实、精明的公司,也有由无知或贪婪的发起人创办的疯狂投机企业。
比特币财库公司的寒武纪大爆发
如今,比特币财库公司呈现出惊人的相似模式;随着全球各地的公司竞相复制 MicroStrategy 的成功,每周都有新的实体公司推出。比特币财库公司的“寒武纪大爆发”可以通过网页数据面板实时追踪:
资料来源:BitcoinTreasuries.net
诈骗黄金时代
创新的开端很快演变为剥削。加尔布雷斯(JK Galbraith)和艾伦(Frederick Lewis Allen)强调,这并非个别不良行为者的时代,而是一个由价格飙升和伦理缺失所驱动的系统性机会主义的时代。
信托热潮中最赚钱的角色不是投资者,而是推广者。加尔布雷斯(JK Galbraith)明确指出,内部人士通过收取费用,既能预先获取价值,也能持续获取价值,而公众买家则承担最终的风险:
公众对投资信托证券的热情追捧带来了最大的回报。几乎无一例外,人们都愿意支付远高于发行价的溢价。发起公司(或其发起人)通常会获得一定配额的股票或认股权证,使他们有权以发行价认购股票。然后,他们立即以更高的市场价格出售获利。
新发行的股票通常以略高于净资产价值的价格发行给内部人士或特惠客户,但许多新发行的股票很快就升至大幅溢价。例如,雷曼兄弟公司(Lehman Brothers Corporation )以每股 104 美元的价格获得了大幅超额认购,相当于购买了 100 美元的资产(但请注意,其管理合同规定将 12.5% 的利润作为管理费支付给雷曼兄弟;其真实的净资产价值可能只有 88 美元)。公开交易后,该基金立即升至每股 126 美元。组织者不仅从每股 4 美元的差价和未来高额管理费用中获利,还以优于公众的条件成为了重要的初始投资者。此外,他们还保留了一项权利——当基金以折价交易时无甚价值,但当基金以溢价交易时却非常宝贵——即以当前净资产价值购买新股份的形式收取管理费用。
与 1920 年代的信托类似,如今的比特币财库公司通常也采用类似的安排——创始人配股、内部股票期权以及为推广者和播客提供的激励方案。然而,这一次,这些机制是根据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规则下公开披露的,而这些规则正是为了应对 1920 年代的滥用行为而设计的。但透明性既无法消除风险,也无法消解激励扭曲:
1920 年代,投机狂热和信托公司成立的迅猛速度,为那些意图不轨的发起人的滥用职权提供了绝佳的掩护。不正当投资信托和控股公司结构的泛滥,体现了加尔布雷斯(JK Galbraith)所认为的 1920 年代金融过度行为的典型表现。他指出,美国企业“接纳了异常数量的推广者、贪腐者、骗子、冒充者和欺诈者”,并将这一现象形容为“一场企业盗窃的洪潮”。艾伦(Frederick Lewis Allen)也对此表示认同:
只要价格上涨,人们就可以心安理得地纵容各种可疑的金融行为。大牛市掩盖了无数的罪恶。对于发起人来说,这是一个黄金时代,而“他”的名字不胜枚举。
这些观察与其他金融投机和欺诈的狂热时期产生了共鸣,包括当今的“诈骗黄金时代” ,以及约翰·劳的密西西比泡沫等历史事件——我们在“风险炼金术”系列中对此进行了讨论,并在《愚昧的大镜子》The Great Mirror Of Folly (1720 年)中进行了讽刺性地记录。但在彻头彻尾的欺诈行为背后,隐藏着另一种风险——或许不那么明显,但同样危险:信托资本结构设计中固有的结构性风险炼金术。
金融炼金术
有人称之为炼金术,而我称之为估值。
—MicroStrategy首席执行官 Phong Le
资料来源:MicroStrategy
MicroStrategy 提供了一个视频和表格,展示了其资本结构不同层级(股票、可转债、优先股等)的“杠杆效应”——本质上是对比特币价格变动的放大敞口:
迈克尔·塞勒(Michael Saylor)反驳了与 GBTC 等封闭式基金的比较(见此处的第二部分),他指出 MicroStrategy 作为一家运营公司具有更大的灵活性:
有时我看到……一位推特分析师说,哦,这就像之前 GBTC 和 Grayscale 的市盈率跌破 mNAV 一倍的时候一样。他们忽略了一点,Grayscale (GBTC)是一只封闭式基金。而我们是一家运营公司。
[像 GBTC 这样的基金]……没有灵活运营来管理其资本结构……它没有选择再融资或承担杠杆或出售证券、购买证券、资本重组或回购自己的股票。
像 MicroStrategy 这样的运营公司拥有更大的灵活性。我们可以购买股票、出售股票、进行资本重组,还可以通过举债来弥补或解决资金缺口。
然而,这种区别忽略了某种历史讽刺:1920 年代的投资信托开创了资本结构创新,使得今天的比特币财库公司对投资者如此有吸引力,并且在 1920 年代创造了我们今天观察到的同样的反身动力。

正如加尔布雷斯(JK Galbraith)所记录的那样,投资信托已经发展成为一种比 GBTC 等简单的集合投资工具复杂得多的东西——它已经成为一种灵活的公司结构,正是塞勒(Michael Saylor)今天所吹嘘的那种:
投资信托实际上变成了一家投资公司。它向公众出售其证券——有时只是普通股,更常见的是普通股、优先股、债券和其他类型的债务工具——然后管理层根据自己的意愿投资所得。通过向普通股股东出售无投票权股票或将其投票权转让给管理层控制的投票信托,可以防止普通股股东干预管理层的任何可能行为。
1940 年《投资公司法》明确限制了这些做法,正是因为它们在 1929 年大崩盘前的市场投机中被证明非常有效,也非常危险。当 Greyscale 及其律师构建 GBTC 时,他们选择这种形式很可能(至少部分原因)是为了避免根据《40 法案》(1940 年《投资公司法》)进行注册。像 GBTC 这样的基金无法部署 MicroStrategy 的全套工具并非其固有限制,而是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 (SEC) 刻意制定的政策的结果,防止重蹈 1920 年代投资信托过度行为及其后果的覆辙。
1920 年代信托的资本结构与如今的 MicroStrategy 几乎难以区分:两者都发行证券——以 mNAV 溢价发行的股票、债券、可转换债券和优先股——以吸引具有不同风险(“杠杆效应”)偏好和收益需求的投资者。例如,作为 MicroStrategy 融资策略核心的可转换债券,也是艾伦(Frederick Lewis Allen)在其研究中记录的 1920 年代信托的标志:
将信托发行的新债券转换为股票或附上在未来某个时候购买股票的认股权证,使它们具有一种可接受的投机色彩,这种做法成为一种时尚。
1929 年经济繁荣时期,许多投资信托的商业模式与其说植根于资产管理,不如说根植于金融炼金术。复杂的资本结构和层层杠杆并非仅仅是提升回报的被动融资工具,而是企业的核心。其目标是创造源源不断的投机性证券供应,以满足永不满足的公众需求。这种需求的动力源于一种信念——加尔布雷斯(JK Galbraith)抓住了这种信念——即信托购买的标的股票已经获得了某种“稀缺价值”,而最抢手的股票即将从市场上彻底消失。
然而,公众购买的并非仅仅是稀缺股票的多元化投资组合,而是对信托自身金融炼金术表现的押注:真正的“产品”是信托自身的证券和资产净值。它们就像炼金术实验室,将公众对投机收益的渴望转化为凭空变出的新证券。
睿智的长期债务
这种类似 MicroStrategy 的策略让 1920 年代的信托经理能够获得优质杠杆:长期公司债券(有时长达30年),而不是那些需要立即清算的保证金贷款或“活期”贷款。理论上,这些延长的期限使得信托能够在整个商业周期中保持杠杆率,而无需面临即时的再融资压力,而其相对较低的收益率则反映了投资者普遍的自满情绪和系统性的风险错误定价。
Lyn Alden 对当代比特币财库公司也做出了类似的观察:
与对冲基金和大多数其他类型的资本相比,上市公司可以获得更好的杠杆。具体来说,它们有能力发行公司债券……通常期限为多年。如果它们持有比特币,而价格下跌,它们无需过早抛售。这使得它们比依赖保证金贷款的实体更有能力抵御市场波动。尽管仍有一些看跌情景可能迫使公司清算,但这些情景将导致熊市持续更长时间,因此发生的可能性较低。
长期债务与反身性
Lyn 的上述分析——虽然对任何一家公司而言都准确——却忽略了这些“更安全”的杠杆结构激增时可能出现的系统性风险。正如 30 年期长期抵押贷款未能阻止 2008 年金融危机一样,任何长期债务都无法从本质上消除系统性风险,甚至可能加剧风险。
在 1920 年代末的繁荣时期,金融炼金术通过与如今比特币财库公司受益的相同自我实现预言放大了回报:资产价格上涨和 mNAV 溢价带来了更高的杠杆率和“杠杆效应”,进而进一步推高了资产价格。但这种反身循环使得系统本质上不稳定。正如我们所见,这些复杂的资本结构远不止是被动融资工具——它们在助长泡沫惊人的膨胀及其随后的崩溃中都发挥了不可或缺的作用。
就像在连续几个平静的风暴季节之后,廉价的飓风保险刺激了建筑热潮一样,牛市中定期到期债务看似安全,却可能鼓励人们提高杠杆率,从而制造更大的仓位和资产通胀,最终放大而非抑制下行波动。新发现的“负担得起的”强制清算保护措施引发了海滨地区冒险行为的惊人扩张——直到不可避免的飓风来临,保险市场本身崩溃。当成百上千家公司采用相同的资本结构和商业模式,进行“单向押注”投机时,个别情况下看似审慎的做法,很容易变成集体性的不稳定因素。在金融“进步”中,剂量决定成败。
路径依赖与金字塔骗局
就像 2005-2006 年间一些设计得几乎注定会在首次付款时违约的极端抵押贷款一样,在 1920 年代泡沫接近尾声时,许多投资信托从一开始就实际上是金字塔骗局的变种——依赖新的资金流入或价格上涨来履行义务——尽管持有多元化的派息股票和付息债券投资组合:
其中一些公司……资本过于雄厚,甚至无法用所持有证券的收入来支付优先股股息,而只能几乎完全依赖盈利的希望。
这造成了一种不稳定的依赖关系:为了支付债券持有人和优先股股东的收益,信托要么发行新股(依赖于其 mNAV 溢价),要么指望未来的投资组合升值。这两种机制相互交织:投资组合收益推动 mNAV 溢价上升,进而促使发行更多股票,为投资组合的进一步扩张提供资金。
本质上,他们利用新投资者的资金或未来的价格升值来偿还现有债务——这是典型的金字塔骗局结构——这使得他们在新资本枯竭、投资组合收益蒸发时容易受到市场低迷的影响,导致他们的 mNAV 溢价在自我强化的螺旋中崩溃。
由于比特币财库公司(目前)没有现金流,因此它们倾向于遵循类似的策略,即从投资者那里筹集资金来偿还债务:
与 1920 年代的信托类似,这种金字塔式的策略在比特币升值、公司维持其资产净值(mNAV)且资本市场对其保持开放的情况下有效运作。然而,如果所有这些条件在较长时间内同时恶化——可能是由于过度扩张的杠杆化比特币财库公司本身造成的——这些公司将面临与 1920 年代信托遭受毁灭性打击时相同的结构性脆弱性。
事实上,1920 年代的投资信托与如今的比特币财库公司之间的一个主要区别在于它们实际持有的资产。这些信托持有(看似)多元化的投资组合,包括派息股票和付息债券,这些投资组合产生的现金流为其优先股和债券的偿付提供资金——至少在大萧条时期,由于普遍存在的信贷泡沫,它们之间存在着关联。
虽然“超比特币化(hyperbitcoinization)”和“比特币银行”未来或许有机会改变这种格局,但比特币目前既不产生现金流,也不支付股息,也不产生利息。这造成了一种结构性脆弱性,而 1920 年代的信托尽管存在诸多缺陷,却从未面临过这种脆弱性。比特币财库公司甚至缺乏 1920 年代信托的收入来源,因此更容易受到这种金字塔动态的影响,而非更少。即使在比特币升值十倍的长期牛市背景下,它们的生存能力也完全取决于路径,取决于持续升值、信贷渠道以及投资者的热情。打破这一链条——可能是由于杠杆化比特币财库公司本身的过度饱和——最终导致结构瓦解,我们将在本系列即将推出的第四部分中讨论这一点。
信托崩溃与1929年金融大崩盘
著名耶鲁大学经济学家欧文·费舍尔(Irving Fisher)曾说过,在 1929 年股市崩盘前夕,股价已经达到了“永久保持高位”。费舍尔(Irving Fisher)的这番言论体现了市场触顶时通常所特有的那种欣快自信。即使是最狂热的比特币多头,至少在短期内,也应该警惕类似的笼统论断:
费舍尔(Irving Fisher)关于市场“高位”的名言如今已广为人知,但其鲜为人知的背景却揭示了更深层次的故事。他实际上是在为投资信托辩护,认为它们是股票估值的重要支撑,就像今天比特币支持者提到比特币财库公司内置需求一样。《纽约时报》当时如下报道:
费舍尔(Irving Fisher)教授就投资信托这一主题发表了演讲,并针对近期对投资信托的攻击为其进行了辩护,这些攻击指责投资信托应对当前的许多弊端负责。
费舍尔(Irving Fisher)为信托辩护,理由是这些工具正在唤醒人们认识到股票相对于债券的优势,并为投资者提供获得股票敞口的更优越的结构——就像比特币资金倡导者今天声称 MicroStrategy 提供了比直接持有比特币更大的“杠杆效应”,而比特币本身也比法定货币、股票、债券和房地产等传统金融资产(TradFi)资产更具优势:
我认为投资信托的原则是合理的,公众参与其中也是合理的,但要充分考虑管理者的品格和声誉。很大程度上,正是由于投资信托运动的影响,公众才逐渐意识到股票比债券更具吸引力。而且我相信,总体而言,投资信托的运作有助于稳定股市,而不是加剧其波动。
反身性是双向的!
股市崩盘不仅仅是一次价格事件——随着反身循环的逆转,推动股市繁荣的动力放大了资产市场和实体经济的衰退。欧文·费舍尔(Irving Fisher)一周前还大力倡导的投资信托,声称其能够保证股票价值“永久保持高位”,如今却成了这场崩盘的主要推手:
到现在,显而易见的是,投资信托,曾经被认为是支撑经济高位的支柱和防止崩溃的内在防御手段,如今却成了深重的弱点。两周前人们还对杠杆作用津津乐道,甚至充满热情,如今却完全逆转了。
它以惊人的速度将一家信托公司普通股的全部价值卷走。和之前一样,一个典型的小型信托公司的情况值得我们思考。假设该公司持有的公众证券在 10 月初的市值为 1000 万美元。其中一半是普通股,一半是债券和优先股。这些证券完全被其持有证券的当前市值所覆盖。换句话说,该信托公司的投资组合中包含的证券的市值也为 1000 万美元。
这类信托持有的代表性证券投资组合,在 11 月初,其价值或许会缩水一半。(以后来的标准来看,许多此类证券的价值仍然相当可观;11 月 4 日,Tel and Tel的最低股价仍为 233 美元,通用电气(General Electric)为 234 美元,Steel为183美元。)新的投资组合价值 500 万美元,仅够弥补先前债券和优先股的资产损失。普通股将一无所有。除了那些并不乐观的预期之外,它现在一文不值。这种几何级的残酷并非个例。相反,它对杠杆信托的股票影响巨大。到 11 月初,大多数这类信托的股票几乎已经卖不出去。更糟糕的是,许多这类信托的股票在场外市场或城外交易所交易,那里买家稀少,市场交易清淡。
弗雷德里克·刘易斯·艾伦(Frederick Lewis Allen)的记述再次证实了加尔布雷斯(JK Galbraith)的说法:
然而,恐惧并没有拖延多久。随着价格结构的崩溃,人们突然蜂拥而至,想要逃离。到了上午 11 点,证券交易所的交易员们已经疯狂地争先恐后地“抛售”。早在滞后的行情自动收录器能够预判情况之前,电话和电报就已经传来了市场即将触底的消息,抛售订单的数量也翻了一番。领头股在两次抛售之间下跌了2个点、3个点,甚至5个点。跌,跌,跌……那些本应在这种时候出手相救的逢低吸纳者在哪里?那些应该通过低价买入新股来为市场提供缓冲的投资信托基金又在哪里?那些宣称仍然看涨的大庄家又在哪里?那些被认为随时能够支撑价格的强大银行家又在哪里?似乎没有任何支撑。跌,跌,跌。交易所大厅里传来的喧闹声已经变成了恐慌的咆哮。
因此,我们永远不应该忘记,反身性是双向的,它不仅会影响基础资产的市场价格,还会影响基础资产的基本面:
企业最重要的弱点在于其庞大的控股公司和投资信托的新架构。控股公司控制着公用事业、铁路和娱乐业的大量领域。与投资信托一样,这些领域也时刻存在着反向杠杆带来的毁灭性风险。尤其是,运营公司的股息用于支付上游控股公司债券的利息。股息的中断意味着债券违约、破产以及架构的崩溃。在这种情况下,为了继续分红而削减运营工厂投资的诱惑显然非常强烈。这加剧了通货紧缩的压力。而通货紧缩反过来又会抑制盈利,并导致企业金字塔的倒塌。当这种情况发生时,进一步的裁员将不可避免。收入被专门用于偿还债务。借款进行新的投资变得不可能。很难想象还有哪个企业体系比它更适合持续并加剧通货紧缩的螺旋……
股市崩盘也是利用公司结构弱点的一个极其有效的方式。位于控股公司链末端的运营公司因股市崩盘而被迫缩减开支。随后,这些系统以及投资信托的崩溃实际上摧毁了借贷能力和投资贷款意愿。长期以来看似纯粹的信托效应,实际上迅速转化为订单下降和失业率上升。
此次危机不仅仅摧毁了纸面财富,还揭露了被债务驱动的资产价格通胀所掩盖的实体经济中的不良投资,并迫使不可持续的商业模式和债务结构进行痛苦的清算。
即使在结构性长期牛市的背景下,比特币财库公司也面临同样的风险。如果比特币大幅下跌(可能是由于财库公司自身的过度杠杆和投机行为导致),并且资产交易价格长期低于资产净值,那么普通股可能会像 1929 年的信托份额一样被彻底消灭,尽管它们的杠杆率是“安全的” 。此外,正如我们将在第四部分讨论的那样,比特币财库公司的激增和随后的崩溃甚至可能在一段时间内对比特币本身的采用产生负面影响。
生于 mNAV,死于 mNAV
如果我们是一家运营公司,并且我们的交易价格低于资产净值,那么我们就可以将其货币化——这对我来说是好事。
—迈克尔·塞勒(Michael Saylor)
塞勒(Michael Saylor)对将资产净值折扣货币化的信心(对于 MicroStrategy 来说,这可能本身是合理的)反映了 1920 年代信托经理用来证明回购合理性的相同逻辑,但后来发现,当整个生态系统的流动性消失且抛售压力占主导地位时,这种支持策略是无效的。
这些信托发现,在投资者抛售、信贷紧缩的情况下回购股票与在投资者买入时发行股票截然不同。为了支撑股价,这些信托开始以低于资产净值的价格回购股票——比特币财库公司很可能会采取这种策略,但大多数公司的结果同样令人失望:
投资信托巨额现金资源的稳定效应也被证明只是幻象。初秋时节,投资信托的现金和流动资源非常充裕……但现在,随着反向杠杆的效应逐渐显现,投资信托管理层更担心的是自身股票价值的暴跌,而非整体股市的不利波动……
在这种情况下,许多信托公司拼命地用其可用现金支撑自己的股票。然而,现在公众想卖出时买入股票,与去年春天买入(就像高盛那样)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异——当时公众想买入,由此产生的竞争推高了股价。现在,现金流出,股票流入,股价要么没有受到明显影响,要么影响时间不长。六个月前还算高明的金融策略,如今却成了财政上的自焚。归根结底,公司购买自己的股票与出售股票完全相反。公司通常是通过出售股票来发展的。
随着危机加深,mNAV 持续折价交易,信托公司耗尽剩余的现金储备,拼命地(最终却弄巧成拙)试图支撑暴跌的股价:
然而,这些都不是立竿见影的。如果一个人是金融天才,对他天才的信任不会立刻消失。对于饱受打击但仍不屈服的天才来说,支持自己公司的股票似乎仍然是一条大胆、富有想象力且行之有效的途径。事实上,这似乎是避免缓慢但必然的死亡的唯一选择。因此,在资金允许的范围内,信托公司的管理层选择了更快但同样必然的死亡。他们购买了对自己毫无价值的股票。人们被他人欺骗的情况屡见不鲜。1929 年秋天,或许是人们第一次大规模地自我欺骗。
结论
1920 年代的投资信托狂热,为理解建立在杠杆、反身性以及溢价/资产净值增长魔力之上的金融泡沫,提供了一个概括性的蓝图。最初的金融创新,很快演变成了投机工具,承诺通过金融炼金术轻松致富。当音乐停止时,那些曾将价格推向欣快高度的反身性机制,加速了其灾难性的下跌。
这与当今的比特币财库公司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从新实体公司的激增,到对资产净值溢价的依赖,再到利用长期债务来放大回报。正如我们在《巴别塔》(Tower Of Babel)中所探讨的那样,2008 年金融危机的主要根源并非次贷危机、债务抵押债券 (CDO) 和抵押贷款欺诈——20世纪20 年代的投资信托倒闭的主要原因并非欺诈、错误的押注、缺乏透明度和监管监督,或其有时相互交织或金字塔式的持股。它们之所以倒闭,是因为它们的成功——建立在“风险炼金术(Alchemy Of Risk)”之上——本身就蕴含着未来失败的种子条件;比特币财库公司或许正走着同样的道路,走向同样的悬崖。
然而,更令人担忧的是,正如 1920 年代的信托标志着那个时代的投机过度一样,比特币财库公司正是当今“多重通货膨胀”的症状——一种扭曲当今经济秩序的更深层次的弊病。一家近期备案的黄金财库公司的出现表明,塞勒(Saylor)和比特币财库公司对法定货币的投机性攻击正在扩展到比特币之外:
这种对货币正统观念的更广泛冲击,或许预示着一场“逃离真实价值”(Flucht in die Sachwerte)的萌芽——这场浪潮有可能升级为一场针对金融机构的全面战争。事实上,黄金财库公司的实际商业模式——将大宗商品市场代币化——可能会通过将更多资金和信贷引入实体经济来加速这一趋势。这非但不能将通胀压力安全地控制在金融矩阵的虚拟赌场内,反而有可能进一步加剧通胀超级周期。
接下来:比特币可以打破反身性魔咒吗?
在第四部分中,我们将探讨比特币独特的货币属性——与央行史无前例的大规模印钞相冲突——是否可能使杠杆资金公司能够通过金融柔术彻底扭转历史格局:引发对法定货币的反射性投机攻击,并创造一个类似于“银行挤兑”的自我实现预言。又或者,它们是否会像 1920 年代的投资信托一样,在其结构中埋下比特币生态的系统性脆弱的种子。